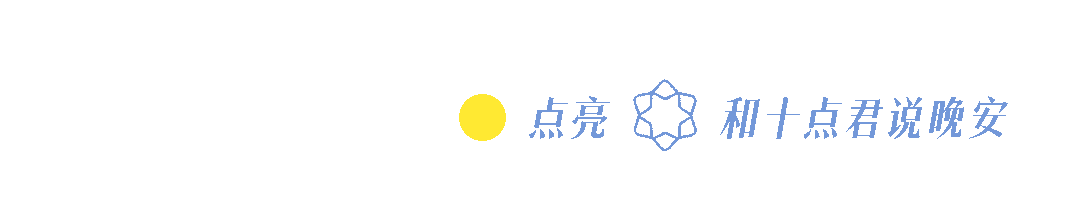在乡镇高中任教不到两年,语文老师吉安已经遇到两起学生因抑郁自杀的事件。
上个月的一个深夜,她的课代表宝嘉突然叫醒宿管老师,告诉她自己服用了过量胃药,要去医院洗胃。
事后宿管阿姨清理现场,才发现宝嘉撒了谎,她服用不是胃药,而是大量的抗抑郁药物。
至于宝嘉抑郁的原因,吉安并不清楚。
她只记得,上个学期女孩曾和自己倾诉过,觉得父母重男轻女,不重视自己。
抑郁症像瘟疫一样在青少年中蔓延。
《2022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》的数据显示:
50%的抑郁症患者为在校学生,青少年抑郁症的患病率已经达到15-20%,换句话说,每五个孩子中就有一个患有抑郁症。
学校方面意识到了心理健康问题的严重性,在年级会议上三令五申,要求老师们关注学生的心理状态,及时沟通,但吉安没有看到任何情况好转的迹象。
面对这些比自己小十三四岁的高中生,吉安感到前所未有的无力。
她不明白:
正值青春年少、学习压力不大的“放牛班”学生,为什么也会陷入绝望?

吉安没有想到,抑郁症会在一所乡镇高中里蔓延。
这里没有太大的学业压力:无论是生源质量还是升学率,这所学校在当地都稳居倒数。
学生不爱学,老师也不勉强,基本采取放羊式管理。“只抓前几名的成绩,其他孩子不影响课堂纪律就行。”
因此,校园氛围格外松弛,大多数学生都在“混日子”。
重点高中争分夺秒,学生去食堂吃饭都得一路小跑,而这里的学生,拥有“奢侈”的休息时间。
上午的大课间有35分钟,午休足足一个小时,可以自由玩耍,不用担心被任何课程挤占。
学校的操场上,几只山羊怡然自得地吃草,课间活动时,学生会来这里逗弄山羊,嬉戏打闹,甚至躺在草地上打滚。

操场的羊|讲述者供图
刚来学校任教时,吉安一度不太适应。
她在郑州一家教培机构工作过一段时间,辅导过的孩子和她说得最多的一个字,是“累”。
他们的暑假时间被作业和辅导班挤得满满当当,“大城市的孩子,教育环境太卷了。我想要是回到乡村,应该会轻松很多。”
然而现实却是,压力不大的放牛班学生,正面临着严峻的心理危机。
作为老师,吉安很难分辨班上哪些孩子患有抑郁症。
上个学期,吉安的学生小霞在家喝了农药。听到消息,她的第一反应是,“这一定是误传。”
在吉安的印象里,晓霞成绩平平,却开朗乐观。
她常来找自己聊天,偶尔会吐槽食堂的饭菜不好吃,要吉安帮她捎个汉堡。
出事前的周一,晓霞还和同学有说有笑,商量考完试之后去哪里玩。谁也没想到,她会在和父母争吵之后突然自杀。
“周三,班上的同学给她发消息,她没有回复,到了周六,就听说已经下葬了。”
年轻的生命像泡沫一样蒸发。吉安反复回忆,试图找出一些被忽视的细节。
思来想去,唯一的可疑之处是,当晓霞一个人坐在座位上的时候,常常会发呆。
可她究竟有什么心事,已经没有人能知道答案了。
抑郁如此隐蔽,以至于当老师察觉到异常时,学生的病情往往已经相当严重。
吉安的学生宁杭就是如此。她性格温和,从不顶撞老师,是班上少数几个有望冲刺本科的好苗子。
上个学期,因为数学课上看小说、英语课上走神,她接连被老师批评了几句。
这本不是什么大事,但课上到一半,英语老师发现,她竟然将自己的一只手抠得鲜血淋漓。
英语老师被吓坏了,强烈要求学校的心理老师介入辅导。
几次辅导之后,宁杭稍有好转,但过了没多久,被地理老师批评后,她硬生生用圆规戳破了自己的手心,血流得整本书都是。
“放在以前,学校的老教师会怀疑,是不是故意在威胁老师。
但这两年,孩子们的心理问题越来越严重,老教师们也转变了思想,意识到孩子们确实生病了。”

下雪天,打雪仗的学生们|讲述者供图
一个班级里有孩子患上抑郁、甚至自残和自杀,就像巨石砸入水中,在其他孩子心里掀起滔天巨浪。
吉安的表弟就读于一所市区重点高中。
疫情期间,他目睹了一位同学跳楼自杀,不久后,最好的朋友也突然离世,接二连三的打击,让他的情绪陷入谷底。
直到他在课堂上一页页撕毁教科书,老师们才意识到不对劲,这个一向用功的学生,已经重度抑郁。
吉安任教的班级里,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。
她的课代表宝嘉因为抑郁症办理了休学,在这之后,班里一些看上去性格开朗的学生,也展现出抑郁倾向,有一名同学甚至办理了退学申请,不再上学。
或许是因为负面情绪的传导,并不会传染的抑郁症,影响了吉安的班级。
对比自己和学生们的成长轨迹,吉安想不通,为什么他们会出现心理危机。
“他们大多出生在2008年前后,和我这种90后相比,家里的物质条件要富裕得多。父母比较年轻,重视教育和陪伴,没有让孩子成为留守儿童。”
可为什么,这些孩子还是会觉得人间不值得?

心理咨询室里,只有沙糖和心理医生两人,他们正在进行精神分析治疗。
在此之前,沙糖经历过三次自杀。
这是一次改变沙糖想法的对话。心理医生提问:“当你听说有人自杀,你会有什么感受?”
沙糖思索了下,给出的答案是:“我很羡慕他,因为他很勇敢,能选择自己的人生。”
而普通人的反应,往往会是惋惜和心痛。
心理医生将两种回答做了对比,沙糖才发现,自己和他人的认知存在着巨大的偏差。
在昔日的老师和同学眼中,沙糖是“绝对不会抑郁”的孩子。
她是典型的三好学生:学习成绩名列前茅,经常拿下年级第一,不止琴棋书画,乒乓球和羽毛球也很擅长。
她还是少先队队长、优秀班干部和学生会主席,参与活动时,永远是手举得最高的“社牛”。
但父母却觉得,沙糖离优秀永远差一大截。考试满分只是正常发挥,一旦失利就要挨上一顿棍棒, “没有表扬,只有批评。”

沙糖要吃的药|讲述者供图
早在小学二年级,沙糖就开始出现胃疼的症状,妈妈却觉得她是故意装病骗取关心,把她痛骂一顿。
那是她第一次产生自杀的念头,鬼使神差地站在阳台窗户边,“我也不知道站了多久,然后我妈进来了。她问我干嘛,我说我想跳楼,她说,你爱跳就跳,想死我也不管你”。
沙糖觉得,在屋顶徘徊过的孩子,或许并不懂得生死的重量,只是在那个瞬间,活着是不可承受之重。
抑郁症是慢性病,如果缺乏相关知识,很容易忽视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——比如头痛、胸闷心悸、肠胃不适、失眠等躯体化症状。
小学和初中阶段,沙糖一直被不明原因的胃痛折磨,她做过胃镜,也查过CT,却始终找不到原因,只能靠一天三顿的中药调理。
到了高中,她的症状突然加重。
高二时,沙糖的记忆力和注意力忽然衰退,“明显感觉自己变笨了,却找不到任何原因”,成绩因此一落千丈。
她开始嗜甜,每天要吃二十几颗糖,否则就会异常焦虑。即便如此反常,沙糖也没有往精神类疾病的方向联想过。
再者,她不愿将朋友当做情绪废品桶,遇到烦恼只会向日记本倾诉,大家觉得她阳光自信,也不会将她和抑郁症联系起来。
老师们最常挂在嘴边的鼓励是:“等你们上了大学就轻松了。”
到了大学,卸下压力的沙糖却突然爆发抑郁症。
她整夜整夜地失眠,不明原因地流泪,直到这时,才意识到自己出现了心理问题。
内心的苦闷到达极限,加上无效治疗没能控制住病情,沙糖吞药自杀,被送到医院。

沙糖住院期间|讲述者供图
后来病情无法控制,几经辗转,沙糖住进上海精神病院。接受治疗期间,她参与了一项学术研究实验。
实验对象被分为了两组,一组是过自残行为的抑郁症患者,一组是心理健康的正常人,分别进行疼痛耐受度测验。
利用红外线灼烧手腕内侧的敏感神经,同时要求实验对象记录下自己的心情指数。
“一般到了7.8级的时候,疼痛感就如同针刺,正常人至多只能忍耐到17级,而且每次灼烧,心情会明显变差。
但有过自残经历的人,在实验过程中能忍耐到20级,手都烫冒烟了,心情却会变好。”
当心理的痛苦无法宣泄,抑郁症患者会向自己的肉体挥刀。
伤痛刺激内啡肽分泌,缓解痛觉,也让人产生一种愉悦感,用沙糖的话说,自残是“快乐”的。
她甚至在实验时要求医生多烫几个地方,“疼痛是会上瘾的。”

经过长达七年的抗抑郁治疗,沙糖已经算“抑郁症的半个专家”,不少病友会找她交流看病和吃药的注意事项。
其中不少是还在读书的青少年,他们问的最多的问题是,看病需要多少钱,能不能自己一个人去?
面对抑郁症时,这些孩子和曾经的沙糖一样,孤立无援。
《2022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》的调查结果显示,46%的抑郁症学生患者没有寻求过任何帮助。
沙糖第一次看心理医生,也是独自前往。哪怕和父母身处同一个城市,她也没有告诉他们这件事。
患有抑郁症的孩子,背后往往有一个生病的家。据蓝皮书数据,69.57%的孩子因家庭关系抑郁。
父母是否重视、能否及时关注和引导,愿不愿意做出改变,都会影响孩子病情的走向。
在乡镇,部分家长的观念仍然趋于落后。
宁杭在班里自残后,班主任建议家长带她去医院治疗,但宁杭的父母死活不肯点头,“我们家孩子没有病,她只是有些走极端了。”
类似的声音还有:“这孩子就是矫情”“她就是故意装病,不想上学”。
家长的顾虑也不难理解。
高考是人生的关键一战,如果孩子被确诊抑郁症,办理休学,复学可能会遇到诸多困难,比如跟不上大家的学习进度,抗拒人际交往。
相较于休学,他们宁愿把头埋进沙子里,装作无事发生,熬过高中三年。
更何况,在偏僻的乡镇,人们往往将抑郁症等同于精神病,病耻感强烈。
宝嘉的父母正是之一。宝嘉在宿舍服药自杀后,被送到医院洗胃。
鬼门关上走了一遭,老师们猜测,她至少要在家休养一个月,没想到过了两天,宝嘉就被父母送回了学校。
班主任生怕会重蹈覆辙,不敢再让宝嘉住在学校宿舍,劝说她的父母在学校附近租房陪读。
可他们怎么也不肯点头,坚持说宝嘉只是得了胃病,误服了胃药。学校和老师也无可奈何,直到宝嘉无法承受学业压力,才选择了休学。
而那些愿意带孩子去医院检查的家长,也可能因缺乏相关知识挂错科室,耽误治疗。
每次看到患抑郁症的孩子在社交平台上求助,沙糖都会到评论区留言提醒: “去精神科治疗,千万不要去心理科。”
这是沙糖差点用生命买回来的教训。
“心理科医生比较擅长心理咨询,精神科医生毕业于临床医学专业,在药物方面更为专业。
如果是失恋,出现抑郁情绪,可以找心理科医生咨询,但如果已经出现了躯体化症状,就要去精神科,进行药物治疗。”
沙糖第一次自杀未遂,被送去心理科,每天被迫接受痛苦的电击治疗,病情非但没有起色,反而越来越重。
“电休克疗法对双相情感障碍比较有疗效,但我是重度抑郁症,对我其实没有太大作用。加上医生开的药不对症,病情一直耽误下去。”
直到在上海住院,医生给她调整了药物,才控制住病情, “这考验的就是医生的药理学专业知识,一开始就要走对科室。”
抗抑郁是一条漫长的道路,孩子们无法独自走完全程,家长、老师、朋友都是重要的陪伴者和支持者。可是学校和老师,究竟能做些什么?
2023年印发的《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(2023-2025年)》明确提出:
到2025年,配备专(兼)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学校比例要达到95%,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比例达到60%。
吉安所在的乡镇中学,也有了心理健康咨询室。每学期,学校都会请心理专家开展心理科普讲座,组织师生学习。
但效果并不理想,孩子们宁愿埋头看小说,也不愿意抬头听讲。即便真的有烦恼,也很少向心理老师求助。
“他们会担心自己在咨询室里说的话,会传到班主任的耳朵里。”
吉安是语文老师,相较于其他科目,语文更重视情感与表达,她的课堂气氛也轻松活泼一些,比如介绍作者生平,她会特意穿插一些有趣的小故事。
或许是因此,许多学生会把她当做知心朋友和倾诉的对象。
她的另一位语文课代表风灵,上学期因为抑郁症办理了退学手续,没有再继续读书,南下去了广东的电子厂。
临行前,她给吉安发送了一条长长的微信:

学生发来的微信|讲述者供图
吉安无法解答风灵的困惑,学校也无法解答。
平心而论,在应试教育体系内,这所乡镇中学的氛围已属宽松,“我们学校只有六百多人,在管理上相对来说更有精力一些。如果遇到有抑郁症的孩子,校方也会尽可能帮助,不会立刻强制休学。”
而在竞争更为残酷的县中、市重点中学,学生一旦出现抑郁症状,会被立刻劝退,就像吉安的表弟那样。
抑郁的学生回家了,但所有人都知道,问题并没有解决。
宝嘉自杀未遂后,吉安写了一篇寄语,安慰孩子们: “人生路还长,慢慢走,不要慌。”

吉安的朋友圈|讲述者供图
许久没有联系的风灵在朋友圈下评论:“现在才知道,万卷书不好读,万里路也不好行。”
脱离了教育的樊笼,孩子们的困惑依旧没有消失。
作者 | 谈心社社长,谈心社(ID:txs163)
主播 | 绛染 ,电台主播、爱配音,神秘的爱猫人。